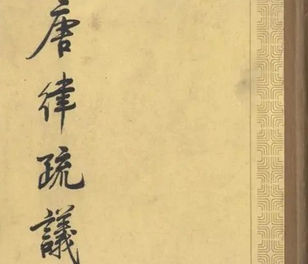《海国春秋》第六回:隐士避功名奚啻阱陷 忠心甘节义尤切神魂
《希夷梦》是清代汪寄著白话长篇神魔小说,又名《海国春秋》,四十回,成书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前。此书叙述赵匡胤黄袍加身,举朝归顺。唯韩通全家殉难,李筠起兵讨逆而兵败自杀。韩通弟韩速,李筠幕宾闾丘仲卿,为复仇而投南唐。南唐君臣不思谋国反思媚敌,韩、闾丘离唐往西蜀,途经黄山,被引入希夷老祖洞府。二人安寝石上,乃得一梦,仲卿到海国浮石,韩速到海国浮金,二人各为其主,既立军功又肃吏治。然才过五十年,却遇陆秀夫抱幼主投海,知中原已历三百载,赵氏国亡,元人入主中原。韩、闾丘惊梦,遂从希夷仙去。作品以洋洋50万言讲述一梦幻故事,前所未见,实是作者的一种创造。总之,全书结构、布局比较新颖,故事情节也颇曲折。那么下面历史网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第六回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且言这个霹雳,震响非常,人俱慑伏。仲卿定睛看去,却是子邮猛然大怒发喊的神威,檐瓦俱为坠地。这声未了,浑身铁绳麻索,尽行脱落。大步直前,抓着防江使肩膊问道:“认得俺么!”
防江使忍痛不过,连声应道:“认得韩爷爷!”
子邮道:“认得便怎样?防江使道:“上命差遣,不能由己。”
子邮见众兵已取到器械,乃带着防江使走来,扯断仲卿身上绳索,问防江使道:“你这狗官,要命不要命?”
防江使道“韩爷爷,命哪能不要的么?”
子邮道:“你不要命,我就用你作家伙抵敌。你若要命,可将船收拾好了,送我们过江。”
防江使道:“遵命,遵命!军士们快选好船,送二位爷爷过江。”
众兵答道:“现成。”
子邮请仲卿先行,问道:“行李驴子在哪里?”
军士道:“俱好好的在此,代爷爷送上船。”
子邮仍拿住防江使,叱令军士站开。防江使连喊道:“站开,站开!”
子邮行到江边,见仲卿并物件俱在舱中。防江使道:“已经送至码头,饶放狗官罢!”
子邮道:“再同过江,难道怕无船渡你回来?可快开行!”
水手只得打起帆来。仲卿视防江使道:“后边若再有一船随着,即带你往丹阳去。”
防江使喊道:“你们听着,半只也不许再过来!”
众兵原是骇怕的,见官吩咐,谁不乐从,俱下锚止住。这个船出口,正系顺风,直到东梁山上岸。子邮见波边山脚下有块小石尖,指船内军士道:“叫你看着!”
将石尖几摇,便断下斗大一块。众兵舌头吐出来,收不进嘴。看看防江使睡在舱底,吐的鲜血满身,两眼翻上白视。
二人催驴前行,当晚到芜湖,欲投宿店。仲卿道:“今日不必投宿,吃头饭,喂喂料,连夜赶路罢!”
子邮道:“更好。”
乃进坊子,上了料,再吃饭,付了钱,槽上牵驴出店。连夜直行。
次日中午,到一个地方,见山虽不甚高,而树箐盈途,纡回杂夹。子邮站住道:“兄可前行。”
仲卿催驴先走,愈入愈深。子邮瞻顾之际,忽听得后面呼的响来,乃飞步冲有十余丈远。回头看时,乃是条大汉,手持着根连枝带叶的树干,随亦逐到。子邮笑道:“朋友,你要甚的?”
那大汉道:“可将行李丢下,饶你性命!”
子邮左手指着右拳道:“问他可肯?”
那汉大怒,举树打来,子邮闪开,凑势右脚踏住梢头;那汉尽力上提,不觉折断,因用力太猛,仰面跌倒,随即飞滚爬起,赶上举拳就打。
仲卿道:“兄弟不可动手,看你非凡,有话可好商量。”
那汉止住,道:“尊姓大名?”
仲卿道:“请教。”
那汉道:“小子姓高名怀亮,因由四川投亲往南昌回来,船上遇着蒙汗药,行李俱为劫去,仆从又遭淹死。小于在途,原不用酒,因天暑热,偶饮两杯,受毒较浅,投入水中,逃得性命。因无盘费,故作此生涯。”
仲卿听毕,下驴道:“如此说,是高二公子,失敬,失敬!”
怀亮道:“不敢,请教。”
仲卿道:“这是韩子邮,小弟姓仲名卿。”
怀亮拱手道:“仲先生,夙仰劳名,今幸过瞻。韩先生可是单身大闹汴梁城的韩二哥么?”
仲卿道:“正是。”
怀亮道:“闻在狱中,如何得出?”
仲卿道:“走出来的。”
怀亮道:“可喜,可喜。”
子邮道:“今日幸会,且到前面村店饮三杯。”
仲卿携着怀亮的手行,见草篷内挑出酒帘,乃同入坐。仲卿问道:“此处是何地名?”
酒家道:“唤做蔗田集,是宣州管辖。”
仲卿见店内并无荤肴,问道:“可有下饭?”
酒家道:“只有素菜小饮,要荤自买代庖,要饭买米代炊。”

仲卿道“有甚的荤?”
酒家道:“鸡、鱼、猪肉。”
仲卿取块银子交道:“可都买来。”
酒家出门,又问道:“熟牛肉可要?”
仲卿道:“我们不吃。”
怀亮道:“也好。”
子邮道:“带十斤来。”
酒家答应去了。
三人取水净了面,吃山茶。酒家回来道:“买了十斤牛肉,二十斤猪首,寸斤重的两只母鸡,五斤重一尾鲩鱼,二斗米,仍剩二钱五分五厘碎银,我收了算酒钱柴火罢。”
仲卿道:“听你。”
酒家道:“这肉腌腌作几顿吃?”
子邮道:“都煮起来,腌什么!”
酒家道:“我只说有几天住,恐怕过了今朝集期,明日无有,所以多买。你吩咐尽行办熟,天热坏了,不要怪我。”
子邮道:“多话,谁怪你!”
酒家叫妻子烧火,自己动手宰刮。
仲卿问道:“公子今将何往?”
怀亮道:“欲渡江寻家兄。”
仲卿道:“大公子安在?”
怀亮道:“未知流落何处,渡江访觅不着,则往宾州探亲,再去追寻。”
子邮道:“无有定踪,此往彼来,反多相左,不如居定处所,找人广访为妙。”
怀亮道:“极是。但刻下只身,如此须到宾州冉作道理。”
仲卿道:“此去宾州,亦非数日可到。”
遂于褡包内取出两锭大银,送与怀亮道:“高兄将此以为盘川。”
怀亮道:“仲兄所赐,固不敢辞,但此去宾州,二十金已足盘川,余者无所用之。”
子邮道:“高兄莫要推辞,行李仆从俱无,投亲恐不好看,弟等有余,兄无多虑。”
怀亮乃收入囊。仲卿问西蜀事势,怀亮道:“西蜀难得久了。”
子邮道:“缘何道理?”
怀亮道:“王昭远为政,事虚而不务实,弟与有瓜葛之戚,见其目空今古,引用不才之人,散弃耆老,十分着急。则国事可知。”
仲、韩为之叹息。
酒家盛鱼带酒送上道:“客人先用酒罢。”
仲卿道:“好。”
怀亮道:“今日也应痛饮。”
三人放量快啖。须臾,鸡与猪首、牛肉齐到,酒家道:“请用,饭也好了,吃不完,明日坏了莫要怪我哩!”
仲卿向二人道:“我量有限,二兄不必谦让。”
子邮将牛肉送与怀亮,叫酒家将杯换去,用碗斟酒,盛上饭来。
真个如狼似虎,霎时间,三十斤火酒同莱俱吃得罄尽,惟剩有两升米饭、五斤牛肉。酒家并妻子在旁看见,都惊讶呆了。
仲卿问道:“此处往黄山走哪条路去?”
酒家道:“你们三人再要猛吃,连汤并锅粑都没有了。”
仲卿道:“休得取笑,问尔往黄山走哪条路去!”
酒家道:“西南路路皆可去得。”
仲卿道“哪条路近?”
酒家道:“客人欲何处入山?”
仲卿道:“我由歙州入山。”
酒家道:“这就要过箬岭,到岭头便见黄山了。”
仲卿乃与怀亮道:“高兄,后会有期,前途保重。弟等请从此辞。”
怀亮道:“今日幸逢,深愿终身执鞭相随,遽然言别,肝胆如割。二兄起义之时,弟闻之自千里来投。弟如机缘有合,二兄闻信,亦望降临。”
仲卿道:“敢不敬从。”
怀亮洒泪而别。
二人第三日午后,到得箬岭顶上,望见黄山千峰万嶂,撑拄青天,如屏罗列,如城团簇,云岚隐见,景状非凡。子邮道:“闻李供奉南游,酷爱黄山,遍其中而复周其外,因其攒簇苍翠,似青芙渠,乃自号青莲居士,果若此乎?”
仲卿道:“罗隐《李杜年谱》可据,自然属实。”
叹赏不已,一步步望着峰峦下岭。
行到昏黑,投入宿店,听有两个西客问游山的法则。店主道:“老客要识奇幽异境,须请土人随行,方能得十分之五六。若无指点,只好得其二三。”
仲卿问道:“要得十分,将若之何?”

店主道:“难,难,难!其中不但年年月月景致不同,即日日时时刻刻各别。可十人同游,各见各景,应接不暇,会谈各殊,所谓十分之五六,恐犹虚也。”
仲卿道:“土人如何请法?”
店主道:“不要钱,只要米,每名每天酬米三升,是由来大例。”
那西客招呼道:“老客,我们同请罢!”
仲卿道:“甚好。”
店主去约得土人来,请先付三十日的钱。西客道:“还没有动身,如何就要钱?店主问子邮道:“土人奉陪,例俱先付后找。子邮道:“我们先付就是,三十日米价应银若干?”
店主道:“白银二两。”
子邮称银一两,付与土人之资。
清晨出门,土人收拾行李上鞍道:“这驴只好寄在山脚庵中。”
子邮问是何故,土人道:“山中转折窄险处,人犹难行,牲口如何去得?”
仲卿道:“且到行不得的地方,再作道理。”
乃邀齐西客起身,行到山脚庵下,将驴交与僧人。再将行李减捆负行。石径虽不尽窄,至险隘处,须将身子伏下,攫着石隙,才得过去,子邮道:“驴子幸亏不曾带来。”
土人道:“要是前面到一线天、鯿鱼背、金刚肚等处,更不好走哩!”
土人且行且指,处处奇峰秀岫,怪石异松,哪里记得许多?
这日来到石笋岗,远近苇攒笋簇。旋行半天,见个大峰卓挺在前。土人指道:“此名老人峰,险峻难行。”
西客道:“咱们不上此峰,另行他路。”
子邮道:“千里而来,岂畏高峻?我们要游此峰。”
土人道:“我随哪位客人?”
子邮道:“你陪西客先行罢。”
土人道:“我们文殊院守候。”
仲卿道:“听便。”
子邮乃将行李拿回。
二人直到老人峰顶上,周围俱是层峦迭岫,细看并无洞岩。天色将晚,乃赶下寻宿。谁知峰脚确无寺院,只得在峭崖边歇下。却有几个瓦罐在旁,也有破的,也有好的。仲卿倦了,倚石而坐。子邮取些枯藤,架起两块石头,用瓦罐汲泉水,敲石取火,燃着桔藤,煮开了水。取出束米来,用开水冲下。二人吃了,乃相倚打盹。问这束米从何而来?原系仲卿枕中带的。
如何名为束米?是将好上籼用南烛叶汁拌匀,蒸熟晒干,又蒸又晒,如此多次。每米十斗收束作八升,用开水冲泡,立时还原。仲卿恐救脱子邮路上断粮,故特制备。
当夜二人睡去,仲卿依稀听得微响,惊醒看时,袋口散开,倒在地下。乃叫醒子邮,已是东方发亮,将散米捧入袋内装好了,捆起行李。仲卿道:“我们往前赶路罢。”
子邮道:“不可,今日仲兄只坐在此,待我再寻。”
仲卿依允。二人烹水治饭。吃过;子邮东奔西跑,七高八低,盘旋走寻。直到黄昏,并看不见有洞,只得依然照旧过宿。乃将行李、米囊坐于身下。
仲卿却睡不着,月明照耀,山光映发,万籁无声,另有殊常气象,使人心地爽阴,俗念都消。仲卿散步,观之不足。约有四更时分,远远见有一人下垄,望崖缓步而来,青衣露顶。
仲卿疑非善类,掐指课来得“猿猴献果”,想道:“课既无咎,应有裨益。”
乃放心闪入旁边,观其行止。忽闻乐声繁起,八音互作,仲卿侧耳倾听。再看青衣人也站住不行,渐渐坐下,枕石而歌,亦似听乐之状。
片时间,星稀天白,仲卿绕前细视,却系个大青猿闭目睡着。仲卿见非害人之物,走到石边,牵其臂膊轻遥青猿惊醒欲走,臂为所执,乃用爪解手。仲卿坚持不住,复执其膊,猿又解膊。仲卿乃右手自其右肩上抱下,左手自其左膊下抱上,两手连袖交往,抱得愈紧,青猿双手齐来争解。仲卿喊道:“子邮快来!”
青猿惊慌,背着仲卿望峰峦密处乱跑乱窜,仲卿眼都花了。奔走多时,到个冈上,猿力亦倦,步亦稍缓。仲卿看对面,峭崖如削,猿却仍往石壁边跑。仲卿想道:“如此险地,势不能下,只好任之。”
看看已到尽头,那猿往下直窜。
仲卿心慌胆颤,搂抱不住,猿已脱去,跌滚下冈。忽然止住,睁目看时,乃为松根所拌,上下左右俱系悬崖峭壁,并无容指之处。仰不见顶,俯不见底,惟闻水声潺潺。只得跨坐松根,饿了彩枝嚼咽。
至午时分,隐隐似喊“仲兄”,连忙呼道:“子邮,子邮,我在此!”
这声答应,山凹里面就一直传去,若有数百人口气。
喊声渐近,举首看时,子邮却在对峰顶上,慌招道:“弟在这里!”
子邮俯视道:“兄缘何到此?”
仲卿道:“为猿所戏。”
子邮喊道:“我也不能过来,兄那边并无可行的路。”
仲卿道:“如何是好?”
子邮见垂藤缠结,喜道:“有了,兄耐坐勿急,弟得策矣!”
只见子邮走去复来,如此数次,乃将件东西推下,视之却系根古藤。子邮上面将根缚于石腰,乃两手执着缓缓垂落,互相对面仅有二丈远近,仍往底坠。仲卿道:“子邮哪里去?”
答道:“仍须再下,方可到兄那边。”
约有五丈,往松根仰望,蹬着石壁,正欲借势跃将过来,忽见仲卿坐的树底下,一团黑暗,乃止住脚。定睛看时,却系个石岩,上面似具字形,为苔藓蔓盖,认不清楚。子邮喜道:“仲兄,洞府在此了!”
仲卿道:“在何处?”
子邮乃纵身跃过,右手执定藤,左手攀着松,翻身跨于干上。将下面之藤收起,统结于根株道:“我先往看来。”
又缒下去。
仲卿忍不住,也随缒到岩前。子邮复盘上,扯去苔藓审视,果然是“九州之一洞天,四海无双福地”十二个古篆。下来说与仲卿知道,互相惊喜,入内看时,十分黑暗,旁边半缺如窦,却有亮光。子邮道:“仲兄在后,让弟先行。”
二人走到里面,虽然明亮,奈愈斜愈窄,仲卿不能前进。子邮使出收身束骨法,往前力入。到得尽头,却是个洞口,也望得见老人峰。回来道:“错走了。”
乃同往暗里摸壁缩脚而行。下了九层石阶,大弯转来,始见亮影;复登石梯,渐见光亮。
石梯约有百级,上面平平坦坦,栋宇晶莹,花卉繁盛,竹木皆系丹色。只见一个大猿,坐在石上剥取柏子仁。子邮向仲卿骇道:“兄,可系此物?”
用手直指,金丸飞出,只见那猿不慌不忙,用手中柏子击来,将丸子打落。子邮连指两指,两个金丸联出,那猿用两指捻着一个,用手打落一个。子邮欲向前擒拿,仲卿看道:“不可错误,先前系纯青,此系纯白,得道仙猿,莫误伤也!”
乃走向前拱手道:“猿公请了。”
白猿也起身,将两手交起,似还礼之状。子邮道:“古怪。”
仲卿问道:“陈老仙祖可在洞府?”
白猿两手往后拱去,仲卿乃同子邮往门内走,寂无人声。又进里面,转过第七层,只见上头坐有一人,隐着石几而卧。向前看时,却系老道士,恐防惊动,退将下来。忽闻笑声道:“仲子来也,仲子来也!”
子邮在下面,见个十四五岁头发披肩的童子,自石边洞中笑出。仲卿转身揖道:“吴槐仙兄,弟到了。春间承教,寤寐不忘。前日于临滁,蒙吴贺仙兄教导洞府,今日幸得造谒,何快如之!”
吴槐答礼道:“仲子名隶仙籍,自应归来。但所言蒙吴贺教导于临滁,吴贺并未出山。”
仲卿道:“现有韩子邮同会同宿。”
吴槐拱手道:“这系韩子么?前日令本家湘子在此访家师,未晤而去。”
子邮揖道:“前日与吴贺仙兄盘桓通宵,甚蒙开导。”
吴槐道:“这又奇了,请到后面看来。”
乃引二人从石边转入,却见吴贺睡在窗前。吴槐指道:“这不是么?”
子邮道:“想是昨日归来的。”
吴槐再看脚下麻鞋不在,笑道:“俗心未除,所言不谬,舍弟果出去了。二子所遇,乃其神耳!”
子邮赞道:“仙家妙用,易胜敬羡!”
吴槐道:“凡心脱尽便成仙,微末小事,何足爱慕。”
仲卿道:“老仙师几时方醒?”
吴槐道:“才睡如何便问醒?就系极快,也须三五百年。”
仲卿道:“如此,弟等去也。”
吴槐道:“哪里去?”
子邮道:“有不共戴天之仇未报!”
吴槐道:“仇人是谁?”
仲卿道:“赵氏。”
吴槐笑道:“天之所兴,谁得而废?韩、李二公食禄死事,理所当然,而今已成正果,何必更为烦劳?害韩公者又俱除灭,犹有何仇乎!二子既知赵氏之非,胡昧韩、李之不善?”
仲卿道:“二公为国捐躯,并无背谬。”
吴槐道:“使其不仕,而安于南亩西畴,焉得丧亡性命!惟欲逞其才艺,思量名标麟阁,功垂竹帛,以致身死家倾,后嗣之存如线,安得不归咎于其身?”
子邮道:“大丈夫自应随时建德成名,流芳百世。若人人甘死牖下,天下事孰旨为之?”
吴槐道:“天下事自有天下人为之,何必自我!天下未有我之先,事何人为?我既往之,后事又何人为?总是道德之心,不胜功利之欲,故为饰说,以致自戕其躯。祖师谓:人入仕途,即如鱼游罟内。若沉潜潭底,远翔海外,何致杂酸咸实鼎鼐哉?”
子邮道:“既为男子,不显亲扬名,得毋有负父母,空长七尺?”
吴槐道:“既知显亲,岂不知劳亲?既知扬名,岂不知丧名?菽水承欢,亲心安佚;以禄而养,亲忧得丧。有荣自有厚,有赏自有罚,有升自有降。荣赏升,亲亦止于饱暖;降辱罚,亲岂堪于焦劳?安能终保其禄养,反多伤亲之天年,是显亲反损亲也!才学兼优,居于高位,秉国家之权衡,操生杀之机柄,稍欠纯粹,则为天下所讥,贻羞青史。入学不优,举动乖张者,误国多致丧身。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犹其小也者。”
子邮道:“古圣先贤,皆以致君泽民为教,如足下所言,则皆非矣!”
吴槐道:“生于古时,原应为之。虞夏之后,即不可为矣。使文种长耕于会稽山原,安有属镂之痛?韩信终渔于淮阴岸畔,岂受未央之诛!掳于心血,敌亡国定,良犬乃随狡兔而烹,岂非为欲致君泽民乎!霍光尽瘁,免于其身,而未闻赦免幼丁,以存其家嗣。萧望之已死,而君犹不知,徒然捐躯绝后,何补于国?陈汤、甘延寿立功异域,刀笔之徒翻削其爵,命几不保,岂非殷鉴乎!”
子邮道:“此皆昧于进退,故多此失。”
吴槐道:“又有不然者,伍员之于阖闾,言听计从,褚遂良、长孙无忌可谓得君矣。然而阖闾、太宗以孤托之义,无能辞,卒皆彼虽欲退,其可得乎?”
仲卿道:“师兄之教甚善,弟等非不知之,若未受恩食禄,自然遵教。但相知最深,受恩最重,仇恨更大,揆于理义,俱不能已旷报仇之后,断不恋于爵禄,定相从徜徉于山水也!”
吴槐道:“二子劳矣,且请安歇,醒来再谈。”
乃引入左边石室,只见如床一般大块青石,两头两块小石如枕,并无被褥。仲卿恐其寒冷,吴槐道:“此系石床,峰上移来,为容成老祖下榻。请试睡去,看比细席如何?”
二人坐上,却温和绵软,因奔跑劳过两日,放倒头就睡。
仲卿心烦易醒,辗转久之,不复成寐。子邮鼾声方盛,正欲喊他起来,共论事体,忽闻有人呼道:“亚公,尔好安逸也!”
急答道:“不敢,不敢。”
连忙坐起,只见似人立在户外,却看不清楚,听得声音很熟。慌离石床,出丹房,下阶迎问。
失脚惊醒,方知系梦。坐于地上,细看并无踪影,想道:“好奇怪也,方才明明系潞州呼声,如何却系梦,又如何跌倒在阶下!”
再看星月满天,光彩盈室,竹树参差,地上并无花叶枝柯之影,甚为诧异。信步徘徊,穿径出垣,瞥见对山悬挂白龙,从峰颠飞下,直到涧底,却久久行而不止,更加惊讶。前往视之,却是道飞泉,讶道:“这般大瀑布如何无声,真是奇怪。且看流到哪里去?”
他沿涧岸行走时,忽闻人语繁杂,仰视又见樯桅列徘。近前问道:“此系什么地方,船艘装往何处?”
梢公答道:“此地名大通镇,系水马头,上通楚蜀,下达吴越。”
仲卿道:“由陆入蜀,有盘诘之搅,船中自然好些,且回去招呼子邮同行。”
主意已定,转身就走,到得三叉路口,忘却哪条是来时取行的。细看山川,迥然不同,疑惑愈盛。又想道:“与子邮偕行,难免滋事,且单身先去,约定高兄,再来招他未晚。”
乃复到岸边,问梢公道:“宝船可系入蜀的?”
梢公答道:“是入蜀的,但今日方才到埠,货仍不曾起清,回去尚五日期。前边第三只系今日开的,水手上岸去了,如要进川,可过去问。”
仲卿乃到前边来搭船,梢公道:“你可系仲卿,可系韩速?”
仲卿笑道:“我却姓古名璋,不知什么重轻含缩!”
梢公道:“不是就罢,而今关上要查问哩!客人既非他们,我将鲁香姓名填人票单,就免得过关耽阻了。”
不知船上众人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