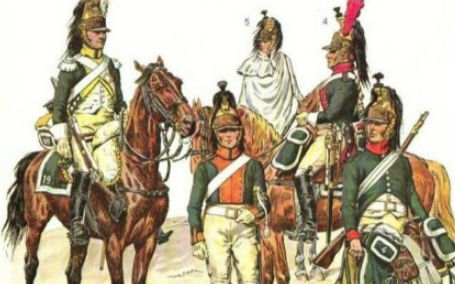大战争小故事(3)——谎言中的胜利(上)
本社全新系列,通过在亲历者的回忆,感受战争残酷与冷暖。
全篇约7000字,为方便阅读分为两部分。

(图为回忆者埃里希海勒)
技术维修主管有一只德国牧羊犬,它坐在桌前,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和宝马摩托车。它是在(SS第1步兵)旅撤走两天后才出现的,然后我想起旅参谋部中有人养了这样一只狗,我就问军医官,我能不能把这只叫雷克斯(Rex)的狗一起带走。他同意了。于是在(1942年)8月15日,我跟在一辆卡车后面向拉特纳亚(Latnaya)和火车站出发了。在那里,跨斗摩托车被装上了平板车,前面则是一辆突击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装备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摩托车——以此提高摩托化水平。
8月18日,我们的火车终于抵达库尔斯克,我的车被卸了下来。在当地的指挥官办公室,我得知自己本应接着坐火车去基辅,但下一班火车要过几天才到,所以我必须先去调动办公室报到,并在我的文件上盖章。在那里,我惊讶地得知,我还要为狗准备通行文件,这样我才能为它领取口粮。经过一番折腾,一位戴着一战时期铁十字勋章的年长上尉为我把一切都办妥了。晚上,我和他还有一位中尉一起去了库尔斯克国家剧院。那真的很有趣,有不少漂亮的女士,衣着优雅,有些还带着孩子坐在包厢里,不过所有人都是由国防军成员陪同的。
在一天午夜前后,我们的火车离开了,向基辅驶去,并于第二天早上抵达。我卸下了车,再去调动办公室报告。在这里,我的通行文件被盖上了前往明斯克的印章,我还为自己和雷克斯领取了口粮,并拿到了津贴和配给券。我得说,德国的行政系统运作得很完美。由于离下一段行程还有两天时间,我就在基辅观光了一圈,那里是我们去年占领的地方。

之后,我终于登上一列开往戈梅利(Gomel)的意大利空火车。在火车上,我得以用一些面包与意大利护送人员交换了一些番茄。我记得当时唯一能吃到的热食是意大利面。两天后,火车抵达明斯克。我向调动办公室报告时,获知我该去步兵旅的 *** 点报告。我马上就找了过去,那是位于鲍里索夫(Borissow)附近的一个村庄,我被命令向(SS)第10(步兵)团报到。

埃里希海勒所加入的正是SS第1步兵(摩托化)旅。与东线早期的几个SS部队不同,他们主要部署在主战线的后方,执行更强残酷的治安战。图为该旅的旅徽。
当我往那里赶时,天已经开始变黑了。所幸道路状况良好,这使得我还能忍受这段旅程。突然,从我右边的树林里传来了步枪的枪声。有两三颗子弹击中了我的摩托车,虽然幸运的是没有击中燃料箱,但有一颗子弹却击中了我的左下臂。雷克斯倒是还安然无恙,它始终蹲伏在挎斗里。我立刻松开油门,飞奔着跑开了。在团指挥所,一位军医帮我包扎了手臂,并给我打了破伤风针。攻击我的人是游击队,他们在该地区很活跃,正威胁着公路和铁路线的安全。我报告说,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进一步的命令,但军医让我休息两天。
此后,又传来再次行动的命令。团从布里索夫(Brisov)向格夏兹克(Gschatzk)行进,然后转向北方。在到达拉科夫(Rakov)前不久,我的摩托车上的变速杆坏了,一个俄国人帮我把摩托车推进一个村子,那里有一位铁匠,他焊接了一个新的变速杆,这个变速杆是如此完美,甚至直到今天,我还对这个人的能力感到惊讶。那时天已经黑了,我不能再冒险继续走得更远了,因为游击队的威胁无处不在。我给了铁匠面包和烟草作为报酬。他的妻子不愿意带我去他们家,因为他们的妹妹和他们住在一起。她可能认为我会骚扰那个女孩,也可能是因为我身上有虱子(我们必须涂抹氧化锌膏来摆脱这些小害虫)。
第二天早上,我加入了一个前往伊韦涅兹(Ivieniez)的纵队。在那里,我见到了我们的联络官,他说10团的位置已经改变,我们要再次向旅部报告。他们对我们的突然出现感到非常高兴。雷克斯和它的勤务官主人无比激动地互相问候,我也因为照顾雷克斯,而得到了一瓶白兰地和一些香烟。但奇怪的是,在接下去的日子里,这只狗只和我一起出行。
1942年9月上旬,在驾驶摩托车穿过一片树林时,连接蓄电池的电线断了。我们站在那里,狗和我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办。几分钟后,我听到孩子的声音,然后一群年轻的男孩和女孩出现了,他们站在那里盯着我们。我意识到该地区一定有一个村子,于是请求这群孩子把我们推去他们的定居地。这很有趣,当村里的成年人看到孩子们推着一辆由一名党卫队突击队员驾驶的挎斗摩托车,还有一只德国牧羊犬坐在挎斗里时,似乎一点也不担忧。老村长被叫来了,他(用德语)向我问候道:“您好,亲爱的。”
没有人比我更惊讶了。我下了摩托车,上前和他握手,并问他怎么会说德语的。他笑着告诉我,他会说德语、波兰语和俄语。他参加了1914年的坦能堡战役并被俘虏。他最终在萨尔州(Saarland)的一个农场工作了五年,并说他在被强制拘留期间受到了良好的待遇。他让一个年轻人把我的摩托车装上一辆马车,然后把我带进他的屋子。在那里,他用粉笔勾勒出了他的村子和一个小镇的位置,据他说,这个小镇离这里仅10公里,那里有一支德军部队。不过,他坚持要我们先吃饭再说。
一大锅火腿、鸡蛋,还有一些伏特加被端了出来。我看到一些人开始用报纸和黄花烟草卷烟。我招手让他们过来,并把一包烟草和卷烟纸放在桌上,示意他们拿去卷烟。吃饱喝足后,我问村长,这一带有没有游击队出没。他说,只要他在那里,就不会有游击队。直到很久以后,我才被他含混的话语所触动。(注:海勒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年轻人们把我带去那个有德军部队的小镇。那是一个治安警察连。他们在我睡得正酣时把我的摩托车修好了,然后我加入了一个前往拉科夫的纵队。当我到达那里时,当地的指挥官办公室却不知道我的旅在哪里,并说我应该等着。我领取了自己和狗的口粮后,就做了大部分士兵都要做的事——等待!
第二天早上,我加入了一个补给纵队,前往距离斯卢兹克森林(Sluzker Forest)约30公里的一个村庄。在那里,我得知必须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继续前进。由于受到游击队的威胁,只有在白天和火力充足的纵队才被允许行动。
于是,我和两位四十多岁的女士住在了一起。其中一位总是微笑着,以展示她美妙的金牙。不过,我当时只有19岁,并不觉得四十多岁的女士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接着,越来越多的女士来到这里,然后是德军的下士与中士们。随着一台留声机的出现,一场真正的聚会开始了。由于我喝了不少伏特加,所以我像往常一样,在狗的陪伴下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赶往斯卢兹克(Sluzk)。在那里,我去“士兵之家”(Soldatenheim)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我记得很清楚,吃的是意大利面和炖牛肉。因为没有别的行程更远的纵队了,我只好独自继续前行。与此同时,我把自己武装得很好。我有手枪、步枪和一挺很棒的芬兰机枪,这是一种极好的武器。我还有一些卵形手榴弹和木柄手榴弹,我把它们都收藏起来了,这样它们就不会被任何流弹击中——毕竟我是一个移动的军火库。

沿着路况良好的道路行驶了几公里后,天突然变暗,然后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我实在无法再继续赶路了,只能在经过下一间农舍前驶离道路,把摩托车直接开到了农舍门口。狗和我一起站在门廊里,浑身都湿透了。我敲了敲门,来开门的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俄国女孩。她突然大笑起来——想必狗和我看着一定相当狼狈。她给了我热牛奶,我还能把湿衣服烘干一下。我给了她一些面包和香肠酱,对此她十分感激。她会说一点德语,我猜测有一支德军的信号部队在这所房子里住宿过,他们目前在斯卢兹克。她有一张该部队所有士官的照片,是这些人给她的。当我站在烤炉前擦干身体时,她把照片拿来给我看。细看之下,我惊喜得几乎陷进去!
在照片的前排,站着我来自科隆的老朋友海尼施密特(Heini Schmidt)。在我担任德国少年队的部队领导时,他是希特勒青年团的部队领导。那是一种真切的喜悦之情,女孩似乎也由衷地为我能在广袤的俄国找到少时的旧友而感到高兴。接着,我向她道别,几分钟后就要上路了,并承诺如果我经过这里,会再来拜访的。

随后,没几分钟我就来到了位于斯卢兹克的信号连兵营。我得到指示,去了施密特与其他两名士官合住的房间。当他看到我时,表情相当有意思。我们有很多吃的和喝的。在那栋特定的房子外面,降下了那场大暴雨,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巧合。
第二天,我去那个女孩家告诉她我的消息。由于天色已晚,我便在那里过了一夜。我们就像兄妹一样相处着。她煮沸并清洗了我所有的内衣,那里面全是虱子。我涂上氧化锌膏来对付虱子,并重新包扎已经开始化脓的伤口。
第二天早上,我加入了一个纵队,并最终回到了我的旅。由于虱子和伤势的缘故,我立即被送进了医院。我当时的状态很差,不过后来有了一点改善。1942年10月底,在康复之后,我设法休了一段时间的疗养假。
。。。
(未完待续)